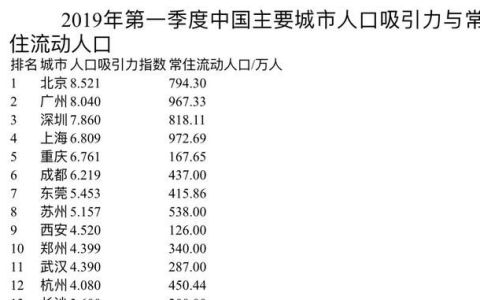在记忆中领悟生活中的况味
我不想,也不愿意去记忆,因为生活中的诸多隐情罢了。它总让我欲罢不能,欲说不休!我岀身于地主家庭。爷爷是个小炉匠,打镰,镢头,门栓子,斧头等農具,后打用鳌子烙馍。爷爷个子高,走路拄着一个胳膊粗的棍棍。这棍棍通体发亮,泛着古气,说穿了,是爷爷手上的汗和油气是此物上了一层釉色了。爷爷话语不多,最爱的是抽旱烟了。
爷爷抽烟,抽旱烟叶子。往往都是,拽一片发黄的旱烟叶子,双手合掌,来回揉搓着,少顷,手心黄灿灿,爷爷一脸陶醉了。一边拿过脚边的长杆铜烟袋,搭在嘴上,试劲吹着,一双脸憋的,干瘪的双腮帮子鼓起干瘪,干瘪有鼓起。有时不通了,干脆用扫地的扫帚眉,从烟袋锅眼眼进去捅捅,便有搭到嘴巴里吹吹,烟锅里发岀丝丝的响声,爷爷便三指头一捏,把烟叶沫儿就势按在烟锅上,随手把保谷胡子拧成的火绳,凑到嘴边,撮起嘴巴,噗一一噗一一噗三口,火绳一亮,赶紧低下头,随着叭哒声,爷爷陶醉了。微闭着眼睛。这是一种幸福安康的完美表白了!
在我人生短暂的岁月中,儿时在紧张莫名其妙中生存着。我总觉得,儿时的我不肆意渲染哪个时候的一切。总想着,不要多说一句话,父亲说,多听多做,爷爷说,咱成份高,多長点心眼子。爷爷说的话,我能记到老。我往往受到贫下中農孩子的凌厉的漫骂,地主娃,地主娃娃子。似乎不叫我这个,就嘴巴缺些什么了。
哪个时候,我家的街房充了公,大队让人在里面弹棉花。棉花机子带电了。轰隆隆的辊子卷着烂稻子,稻子泛黑,颜色也发着黑。整个屋里雾都漫舞,令我十分呛鼻子的响响打着喷嚏不断。往往打喷嚏了,妈妈说,庆娃儿,谁说你了。二姐说,耳朵烧不烧?
不烧。
我用手试着耳朵,令我十分好奇。我很是难忘,往往放学走时,总要扎草喂猪。这猪,大花了四十元买了一头。这猪是尖尖嘴,吃食艰燥死了。用黄瓜十似的长嘴巴,把猪食从猪槽里拱到槽外边拱的‘到处都是!父亲用双手掬着猪食,有放到猪槽中。
父亲在西关二食堂,服务楼,丹江饭店,西街甜食店,饺子馆都当领导。有是会计,有是大厨师。当时,行署,省上面的领导们來义商洛专区开会,都住在丹江饭店里。所以,父亲是常和领导接触的多。父亲擅長商芝炒肉,蒸碗子,甜早肉,等手艺,在饮食服务公司都是年年当先进工作者。父亲毛笔字好,写标语,少不了父亲。记得西街照像馆里有父亲抽纸烟的一张像片,半身像片,很是自然的美。当时在商县城轰动一时。
父亲一生智慧过人,没有什么东西能难到他。父亲乐观,工作上没麻哒。
记得我们姊妹们在王八十沟拾包谷楂,都临黑了,父亲高大的身影闪现,我们欢乐的跳吧!父亲担着一担子包谷茬,一闪一闪,从坡上下去,走过王八十沟,制药厂,商中院墙,农付公司,西关一队场面,老车站,一巷子,进西关街道,过一个电杆,向东,迈房阶,便进了门,父亲把担子放在院子房檐下,一个一个把包谷茬垒起來。窗子下,桃树下都垒满了。
庆娃儿,揽些包谷茬來!煎糊涂饭,快些,肉死了!
在大姐催促下,我抱了一大怀包谷茌。堆放在
灶火里。
还有窝酸菜,这讲究。母亲坐在案边,切着萝卜缨子,红萝卜缨子,父亲担王泉到龙王泉,凤凰泉让大姐淘菜。父亲有担回家到进八斗翁!?母亲切馒菁丝丝,淘洗干净,放进锅里,水一开,,有倒进有酸菜翁里面了。
回忆青春,难忘过去激情岁月。在回忆中渐渐的发现,原来是这样啊!
回头想一想,还真有一件事,让自己刻骨铭心,不能忘记。2004年。儿子参加高招结束,估分应该得625分。儿子最心仪的学校是复旦大学,复旦复旦,成了他高中时段口头禅和奋斗目标。可是到了报志愿,犹豫了。我在一旁参考说,你的分数没有太大的竞争优势,挑战复旦这样好的学校把握不大,不如报一个省级一本学校,把握比较大。结果他放弃了报复旦,走了一个省级一本大学。考分揭晓。622分,理想之中。但获悉复旦大学在河南招生分数线仅仅是601分,儿子惊呆了,我傻了。后悔呀!?很多梦不是实现不了,而是不敢想,初心和愿望往往毁在了自己保守中。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,不但没有帮助儿子托起梦想,反而帮了倒忙。每每想起这件事,惭愧和悔恨交织在一起,五味杂陈,心有余愧。
版权声明:本文来自用户投稿,不代表【爱生活网】立场,本平台所发表的文章、图片属于原权利人所有,因客观原因,或会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,非恶意侵犯原权利人相关权益,敬请相关权利人谅解并与我们联系(邮箱:youzivr@vip.qq.com)我们将及时处理,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创作环境。